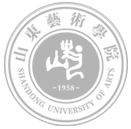郎朗 国际著名钢琴演奏家,首位当选为联合国和平使者的中国人。唯一一位和所有顶级交响乐团合作过的亚洲钢琴家,曾十次获得德国古典回声大奖等多项古典音乐类权威奖项。2008年成立了“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”,十余年来公益足迹遍布全球。2018年,又在中国建立了“北京郎朗艺术基金会”,资助儿童学习音乐。

王歌群 男高音歌唱家,威廉希尔音乐学院院长、声乐教授,第十三届政协委员,山艺欧美同学会会长。毕业于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,与中国、美国及意大利多个城市的歌剧院及交响乐团合作演出。翻译音乐家巴伦博依姆的著作《音乐让时间苏醒》,由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王瑶 威廉希尔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,中国钢琴专业学会理事,山东钢琴专业学会副会长。“全国优秀教师”,学生多人次获中国音乐家协会“中国音乐小金钟”全国钢琴比赛总决赛银奖。受聘山东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硕导及兼职教授。多次公派出访澳大利亚、法国、奥地利进行演出及学术交流。

王歌群、王瑶与郎朗展开访谈。

郎朗(右)指导学生弹琴。

郎朗(右)在钢琴上签名。
在全中国乃至世界学琴的孩子们心中,国际著名钢琴演奏家郎朗都是钢琴音乐殿堂中令人仰慕的存在。与大师同台,接受一对一的专属指导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日前,钢琴演奏家、联合国和平使者郎朗受邀来济,与泉城的学生对谈钢琴艺术。省政协委员,威廉希尔音乐学院院长、教授王歌群与威廉希尔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、教授王瑶现场同郎朗访谈互动,畅谈音乐,郎朗知无不言,分享学艺“锦囊”。
学艺术要触类旁通 把自己融入音乐情境
王瑶:在座的很多学生,是怀揣着郎朗梦而走上钢琴专业学习道路的。今天大家有幸见到您,请问您对钢琴专业的学生有何建议,学生应如何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艺术生涯?
郎朗:我不了解每个学生的状态,但我们可以从宏观上谈一谈,一个音乐家、一个钢琴家要具备的能力和自身的素养。
很多人可能认为弹琴就只能靠练,猛练、狠练,这肯定是其中一个因素,但实际上,一个人开阔的视野和渊博的知识以及对乐曲独特的理解和洞察力,对艺术的敏感度,都值得我们去探究。
对于每个同学来讲,首先要非常努力地去练习,达到一定的时间量,很多学生说每天能练习四五个小时,这段时间里如果练得对,可以练很多独奏曲目,还能练一两首协奏曲。
我和王歌群院长在柯蒂斯音乐学院上学时,见过很多国外的同学也就练四五个小时甚至更少时间,但曲目量已经能练出来了。另外,大家除了对钢琴感兴趣以外,一定也要对别的艺术门类感兴趣,如绘画、雕塑、文学。对时政也要有一些了解,起码要了解一下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,因为我们在演奏作品时,音乐来源于当时的大环境,所以我们对当时的人文环境,包括大的背景,都要非常了解才行,必须把自己置身于这样的情境中,体验这样一种感觉——美好的感觉或者压力或者是一种痛苦,要把自己想象到这样的环境里来。
比如弹贝多芬,就要了解法国大革命,要有一个大概的对时代的判断。同时,作为钢琴演奏者,如果你只谈论弹琴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,因为音乐演奏到最后就已经融入到乐器中去了。
乐器固然很重要,但不管是钢琴还是你的画笔,指挥棒或者是舞蹈,都是在创造艺术。我们不要囿于知识的局限性,固化地看待事情。比如桌上这朵花,我们必须正面看一看,背面再看一看,从多种角度去体会、感受它的美。同样的,演奏作品也是,要用不同的眼光、不同的风格、不同的手段去诠释。
如果局限自己,甚至说弹钢琴发声就应该这样,弹琴不能怎样,这都不是艺术。当你聆听著名钢琴家霍洛维兹弹琴,听古尔德弹琴,或者听阿克里奇弹琴,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对艺术的初心,也不能停止对艺术勇敢地探索,要不断学习。我现在弹柴可夫斯基有几百遍了,但是我希望每次再弹,还是能弹得不一样。千万不要把自己固定到某一个位置上,否则艺术会停滞不前。一个钢琴家,一定要有视野,有自己的判断力,不断去努力、去追求、去探索。
王歌群:从您的讲话里看到您的音乐世界。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钢琴培训学校,请问您的音乐教育理念与体系跟别的学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?您认为钢琴教育或者是音乐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?
郎朗: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所谓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。对于我来讲,对专业学院比较了解,因为我小时候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,然后去了柯蒂斯音乐学院,之后看过全世界很多的音乐院校,在这样的环境中学音乐非常纯正。
把基础打好,这点非常重要。在学校里打好基础,培养青年时期的价值观、艺术观,这是我们在学校里要学的东西。从学校毕业后,我非常荣幸地得到两位非常著名的音乐大师的指点,他们都是钢琴家兼指挥家。一位是阿根廷钢琴演奏者、指挥家丹尼尔·巴伦博伊姆 ,他是一个对哲学、时政都充满热情的人。我原来对哲学不太感兴趣,但自从开始跟随他学习,他永远都会问为什么:“你为什么这么弹?你能不能解释一下?你的原理在哪?你的点在哪?你的理论在哪?”他有很多这样的发问,我后来就开始看哲学书,否则真的没法解答他的问题。
另外一位老师是德国最杰出的指挥家、钢琴家之一——克里斯托夫·艾森巴赫。当时我去柏林一待半个月,听他指挥瓦格纳歌剧,给别的钢琴家讲课,听他的贝多芬奏鸣曲现场音乐会。有时瓦格纳歌剧实在是太长了,我就会坐在乐池里听,在这样的氛围中,我学到了很多实战经验:在舞台上发生什么问题,找到什么解决办法。
真正在舞台上演奏贝多芬,可能与平时练习的时候想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钢琴家鲁宾斯坦会强调这个踏板要怎么踩,这个指法要这样……有些东西在谱子、课本里面也会有,但实战演出时,在音乐厅里,跟顶级乐队交流时,有时就觉得答案离我很远但其实又很近,你会很快地有所感悟。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教育体系,必须要有舞台经验支撑,如果只在家练琴是不可取的。就音乐而言,就演奏家这个行业而言,除了书本上的东西以外,还要不断给学生创造比赛和演奏的机会,要不断地在舞台上、在实战中成长。
职业演奏家要再“长”出一个“心脏”
王瑶:我们知道您的曲目量惊人,有时一年的演出达140多场。想听您谈一谈怎样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效高质量地练琴,并且可以高效地背谱,怎样才能在舞台上稳定发挥?
郎朗:高效练琴确实是个挑战,如果以前在学校里,不用每天坐飞机外出演出,背谱的速度会快一些,不会浪费一些时间。一般来说在琴房里练六七个小时,谱子就背下来了,但是真正变成职业演奏家以后,你得再“长”出一个心脏,这个心脏和你生活中的那个心脏没什么关系。不管你多累、有什么情绪,只记住自己是为舞台而生。很多时候这是个意志的问题,有时出国演出时差倒得迷迷糊糊,还要想一个比较复杂的协奏曲的确很累,但一到排练厅就相当于进入了另一个时空,什么都不能再想,上台就全部切断了。一个成熟的音乐家一定要有一个开关,不能任性,要把自己调整到最稳、最佳的状态。
背谱一定要抓重点。实际上多数曲子都有它的规律,前前后后就那么几段,要特别记住哪里不一样,要给它们特别的关注。我曾请教过巴伦博伊姆为什么可以背那么多谱,他说平常都是生活,转调就像世界上发生了一个危机,是一个高潮。指挥家马泽尔怎么记谱子?当年我问他时,他回复“你知道复印机原理吗?我的脑子就是复印机。”马泽尔有过目不忘的能力,在排练时能闭着眼睛轻而易举地说出哪一页哪个声部有什么问题。大家按巴伦博伊姆的方法练就好,越练脑子越快,不用担心脑子会超负荷。
王歌群:今年您出的新专辑《郎朗的迪士尼》唤醒了很多80、90后的童年回忆,您录制这张专辑的初衷是什么?请给我们分享一下。
郎朗:我一开始是想录一个动画片专辑,但是动画片的曲子太杂了。后来我们想,一些特别好听的旋律都集中在迪士尼,它的IP确实打造得很好,有很多经典的作品,包括有点像民谣的作品,不光是流行乐,像《冰雪奇缘》和一些比较可爱的童话般的作品。那么主要的挑战是,这样的专辑就很容易做得四不像。因为这个旋律要做成纯古典不太可能,但是要做成纯流行,就会感觉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事?所以有时我也比较矛盾。
但我们还是找了很多特别棒的音乐家,包括我自己也进行了一些改编,有些东西听着像李斯特,有些东西听着像舒曼,我们把一些经典的和声技巧都放上,最终呈现效果不错。
5年捐助100所学校 “快乐的琴键”让孩子爱上音乐
王瑶:您的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开放已经有十几年了,国内的北京郎朗艺术基金会也已经走入第5年,捐助了100多所学校。什么样的初心使您那么多年一直在为推动音乐公益事业而努力?
郎朗: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得比较顺的时候是要回馈社会的。我在生活中、旅程中,看到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孩子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足够幸运能成为音乐家,所以我的初衷就是想为这些孩子们建一个更大的、更国际化的舞台,让他们有机会在舞台上发光,让世界都看见。
随着基金会做得更深入、更专业,我又发现有很多有才能的小孩连学音乐的机会都没有,他们连摸钢琴的机会都没有。整个世界上都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,我们必须得重视,这也是为什么我去某个城市,一定要在这个城市比较困难的区域进行音乐交流,让音乐课重返到学校中去,让他们把音乐课作为学校必修课学习的原因。
现如今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,比如说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——有一个风琴,然后大家唱歌,要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在乐器上感受这种快乐。如果感受不到快乐,为什么要去学呢?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课叫“快乐的琴键”。
在国内,我们叫“快乐的琴键”,在国外我们叫“灵感的键盘”。为什么国内、国外项目名字不一样?在西方,大家认为古典音乐是一个伟大的东西,但有点无聊,有点老龄化,一进音乐厅就看到白花花的一片脑袋。我们一定要让年轻的朋友们知道古典乐或者音乐是带有灵感的,它并不是昨天的艺术或者是过时的艺术,而是今天的艺术,所以叫“灵感的琴键”。为什么在中国我们叫“快乐的琴键”?因为在国内,很多人认为弹琴是痛苦的,所以我们直接打“痛处”:弹琴必须快乐!
地址链接:http://app.lhwww.com.cn/yw/66545.jhtml